我不知道要怎么想才是对的,或许这里的某些人能够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和我的丈夫住在一个距离我们成长的家乡大约有七个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家人和朋友仍然生活在我们以前居住的地方或是附近的区域,因此你会常常看到我们驶在那条通往家乡无聊的路上,这样的情形一年会有好几次。我们通常会试着减少开车回家的次数,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见到我们的家人,而是因为我和丈夫一直很努力地想要使我们的房子看起来更好一点。而周末是我们装潢布置的黄金时间,同时也是开车回家的黄金时间。
过去的两年有超多的婚礼举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必须常常返乡参加婚礼。去年,几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必须在周末的时候开车回家一趟,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待更长的时间,幸运的是,今年我们不太需要这样做。在我说得更深入之前,我必须向你们提到,不只有我和我的丈夫,我们还养了一只狗,更准确地说是一只圣伯纳犬,他的名字叫Gatsby,体重大约有150磅,我们总是会带上他一起旅行。
他在车里的时候表现很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乖乖的待在我们为他保留的后座上。在某一次我们开车的旅途中,有些…有些离奇的事情发生了。说实在的,我和我的先生还有Gatsby过着快乐却平淡的生活,我们都是很冷静的人,偏向相信那些经过查证的事物,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会收集各种事实,彼此互相推理论证。我们都不习惯有太多浮夸的想像和不切实际,除非你把我们家墙上那些大胆的油漆配色也列入考量。正是我们的冷静头脑,让这一切事情显得如此诡异。
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已经在这条回家的路上走过好几十遍,有时候为了上厕所、找点东西吃或伸个懒腰活动身体,我们会在沿途停车休息。通常我们会尽量留意停车的地点和环境,即使是在白天阳光普照的时候,但有时候,我的膀胱并不会配合我们精心布置的计划。人们总是会问,Gatsby他是如何做到能够乖乖地待在车上,而我会笑着说,”为了我停车的次数还比我们为了Gatsby停车的次数多”,这倒是真的。对于公共厕所我有着许多焦虑恐惧及被害妄想,但当我真的需要一间厕所时,什么都没有办法阻挡我想上厕所的心。可能是看了太多恐怖电影,也可能是我有洁癖的关系。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往往都是坚持到光线充足的地方,像是忙碌的加油站或快餐店。
有些时候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就像这一次。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了,在去了一趟我们成长的小镇之后,现在我们要回自己的家。这一天我们离开得比较晚,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正常,但有些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Gatsby在后座熟睡着,我的iPod正高声唱着一些奇怪的独立音乐,我的丈夫因为爱我才忍受这些音乐。车外很温暖,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我们一路都开着窗户。
“我想要上厕所。”我对我的丈夫说,他叹了口气。
“有多急?”
“非常急。”
“到下一个休息区还要大概二十分钟。”
“我百分之百确定我没办法撑到二十分钟,可能连五分钟也撑不到。”我的声音比平常高了一些。
“好吧。”他又叹了口气。
“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在这个交流道出口有一间餐厅,我们就去哪里吧,反正我可以再喝一杯咖啡。”
这个男人有时会有圣人般的耐心,应该说大多数时候。我们下了交流道出口,一个陌生冷僻的出口,我们谁都不记得曾经经过这里。餐厅比我们想像中得远,但却是目前最接近我们的东西,在这一秒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个地方能够停下来。和我们平常习惯的停车地点不太一样,这里没有充满明亮灯光,也没有喧闹的人群。虽然并不符合我们平时的要求,但是希望它至少会有个厕所。在相当黑暗的路上行驶了约一英里之后,我们看到了那餐厅的白光。
在这样的深夜,我们并不期望会有很多用餐的客人,但这小餐厅似乎相当的忙碌,停车场里停着几辆汽车,当我们更接近餐厅时可以看到里头走动的人。餐厅内部看起来几乎是全新的,与外表完全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一个人走进去,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为留在车上的Gatsby摇下车窗,向他承诺在我们重新上路之前会带他下来走走,然后我们朝向餐厅走去。
当我们一走进餐厅,欢乐的叮咚声便在我们耳边响起,食物的香味扑鼻而来,我们俩的肚子都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餐馆里看起来挺干净,而干净是我众多要求里最重要的一项。卡式沙发座椅沿着窗户一排一排的摆放,桌子布满在白色和黑色相间的磁砖地板上,有些位子坐满了人,大多都是男人,身材魁梧高大的卡车司机。有些是夫妇一起,有些则是家庭。
餐厅里有一个长条桌,你可以坐在那里,而桌前就是一个甜点展示柜。透过一个窗口可以看到正忙于工作的厨师,以及穿着桃红色连身裙和白色围裙的女服务生。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我们以某种方式时光倒流回到了过去,但我喜欢这个有点复古的地方。我对丈夫露出一个轻松的微笑,低着头急急忙忙地朝厕所走去。
我找到厕所的门推开,在门的另一边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我继续进行当下我最需要做的事。上完厕所后,我去洗手台洗手,天花板上的电灯发出宜人的嗡嗡声。
当时的我正在等待一封从我最好的朋友那传来的短信,因此在离开厕所之前我查看了一下我的电话。真奇怪,我心想。我以为我的手机电量应该是满格的,为什么却关机了?我尝试着要开机却没有办法成功,我内心呻吟着,知道当我们回到车上时我必须将手机插上电源充电。在要离开厕所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在我的周围移动。我被吓了一跳,看了一下四周围,并嘲笑自己的胆小,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在厕所里的只有我自己一人。
我随即推开厕所的门,回头看了一眼厕所里,那似乎比一开始时还要更亮的光线。一如往常地,我那个性外向的丈夫坐在长桌前,旁边坐着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而我的丈夫正在和那老人交谈。我的丈夫总是很友善,他几乎能够在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找到某些优点。当他不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个值得参考对照的标准,因为任何事情会发生都有它的原因。
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但事情看起来就是很不对劲?对我来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刻。店里的光线实在太亮了,而餐厅又太过于安静。用餐的客人似乎都在注视着我们,非常专心地看着。我感觉不太舒服,以我天生内向的性格来说,这并不奇怪。我看了看窗外,看到Gatsby坐在后座,从车上直勾勾地看着我们,这有稍稍减缓我的不安。至少Gatsby似乎并没有被这间餐厅给吓着。
在我丈夫持续与那老人交谈的时候,我仔细地察看甜点展示柜。柜子里的派美得很不自然,在苹果派和樱桃派上有着相当整齐的格状派皮,香蕉派上点缀着蓬松的奶油,柠檬派上的蛋白糖霜看起来有一英里高。由于我的丈夫已经喝了两杯咖啡,于是我向服务生招手,点了两块苹果派。她甜甜地微笑着,熟练地切了两块派,将它们放到外带盒里给我。我往窗外看去,想要确认Gatsby是否平安无事,当我再转过头来时,只见那苹果派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有被切过的样子。我对自己说,这一定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派。
我摇了摇头,走回我丈夫身边,我没在餐厅里看到时钟,所以我试着将丈夫的手机开机,想要确认时间,但我丈夫的手机也开不了机。
“我的手机没电了。”丈夫说完这句话后便继续与老人闲聊。
“我的也是。”我嘴里嘀咕着,觉得真是奇怪的要命。我转过身子,以便能够注意前方那一大片窗户,也让我可以悄悄地观察其他的客人。餐厅里用餐的人数一点都没有减少,每个人都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和我们刚抵达时一模一样的位置。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吃着东西。太安静了。唯一的对话似乎就只有在我身边的这个,我丈夫和老人之间的交谈。
我皱起了眉头。就在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窗户上的倒影,或者该说是窗户上缺少的倒影。我看到我自己,看到我的丈夫,但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人。一直挥之不去的不安感,现在仿佛在我耳边放声尖叫。一定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窗户上没有他们的倒影。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平息我的焦虑不安,并朝着甜点展示柜的方向走了几步,希望这全都是角度的问题。
可惜天不从人愿。我绞尽脑汁,试图想出一个方法,可以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我想到在我的包包里有一个粉饼盒。于是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出粉饼盒,转过身子背对用餐的客人,假装自己是在检查脸上的妆。我能感觉到血色从我的脸上消失。当我对着镜子一看,发现我的背后并没有任何人的时候。我调整镜子的倾斜角度,转动我的身体,然而一切都只是徒劳无功。
在我焦急的想要从镜子里看到这群人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往其中一个女服务生越靠越近。我给了她一个紧张的微笑,但她并没有回应我一个笑容。相反地,她将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非常非常的轻柔,以致于我几乎感觉不到,除了那冷冰冰的体温,非常寒冷。我看着她的皮肤,这不合理,在她的皮肤上没有任何的血色,没有粉红色没有桃红色也没有红色。她很苍白,仿佛在她的肌肤底下没有一滴血液流动。我和她对望,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忧虑,或是担心,又或是警告。
“趁你还能走之前快离开。”她低声说。我的心脏狂跳起来,转向我那还在与人交谈的丈夫。我很快地看了一眼餐厅,注意到那些异常安静的客人正在开始变得蠢蠢欲动。我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支票,并把它扔在柜台上作为支付咖啡和苹果派的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但基于某些原因,我还是付了钱。
“亲爱的,我们该走了,时间很晚了而且Gatsby还在等着我们。”我说,并轻轻地拉了一下他的手臂。我声音里的异样,或者是我拉着他的方式,告诉了他事情大条。他抬起头看着我,我摇摇头想要阻止他说出那些我能在他眼中看到的疑问。
“和你谈话很开心,谢谢你的建议。”他对那老人说。我几乎是用跑的离开了这家餐馆,一到外面,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用力地打开车门,坐到方向盘后面,在我扣上安全带之前我什至没有费心去调整座椅。我丈夫茫然地爬进驾驶座,手中还拿着刚刚买的咖啡。
“我们应该要遛狗。”他抱怨着,并把咖啡放进杯座里。
“不在这里遛。”我回答并且发动汽车。Gatsby的喉咙里开始发出低沉的咆哮声,我的狗狗一向快乐又友善,很少会有这样的举动。我不敢抬头看任何东西,所以我移动排档杆到倒退档位,踩下油门,尘土和碎石飞扬在我们周遭。
“你在做什么?”我丈夫问,当我驶出了停车场,而轮胎撞到了路上的人行道。
“你看!”我对着他大喊,并且第一次转过头看着那间餐厅。刚刚还在餐厅里用餐的客人,现在全部都挤到了窗户边。他们的皮肤病态苍白,眼睛鲜红如血。”快开车!”我的丈夫大喊。我加快速度逃离这个餐馆,偷偷地看了一眼后照镜,却只看到我们身后一片黑暗。我很快地开上高速公路,神经紧绷到了极点,恐惧传遍我的全身。
我丈夫的沉默让我能够将刚刚所看到的事在脑中备份存档。我知道我不应该继续开车,在下一个忙碌的交流道出口,我开进一个加油站。我的丈夫带Gatsby下车散步,在他遛狗的这段时间里他仍然保持着沉默,而我则把汽车油箱加满了油。不想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咖啡和苹果派,我把他们全都扔掉,走进加油站的商店买些别的东西。
“不好意思,请问你能告诉我任何有关那个餐厅的事吗?就是在前一个交流道出口的那个餐厅。 “当我在柜台结帐买了新的咖啡和零食时,我向店员询问。
“餐厅?”店员问。
“那是一个有点可爱又复古的地方,大约在往北九英哩的位置。”我回答说。 “我想它的名字应该是叫做Crossroad Cafe。 ”
“这里并没有一间餐厅叫做Crossroad Cafe。”店员回答,并递给我找剩的零钱。
“你确定吗?那间餐厅看起来很新。”
“我很确定。”我皱皱眉头,抓起袋子和咖啡,转身离开。当我正要走出商店门口时,一个卡车司机拦住了我。
“Crossroad Cafe?”
“你知道吗?”
“它在大约三十年前就被烧毁了。餐厅的门都被锁住,或是被堵住之类的。没有人有办法逃脱,全部在那场火灾中罹难。 ”
“餐厅没有重建吗?”我问,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的肚子里蔓延。
“没有,小姐。”他回答。
“但是,万一你又看到那间餐厅的话,你不应该再停留。他们不会两次都放你离开。”他说完便走向商店的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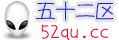
 越南东涛鸡 鸡爪和人手臂一样大
越南东涛鸡 鸡爪和人手臂一样大
 盘点动物界的巨无霸 蓝鲸毫无疑问居榜首
盘点动物界的巨无霸 蓝鲸毫无疑问居榜首
 真正的大长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
真正的大长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
 世界上最大的犀牛 武装部队24小时保护!
世界上最大的犀牛 武装部队24小时保护!
 龙趸是什么鱼?马来西亚发现龙趸王重达400斤
龙趸是什么鱼?马来西亚发现龙趸王重达400斤
 世界上最聪明的猫排行榜 加拿大无毛猫智商爆表了
世界上最聪明的猫排行榜 加拿大无毛猫智商爆表了
 西施狗为什么要叫西施?西施狗多少钱一只?
西施狗为什么要叫西施?西施狗多少钱一只?
 上户蜘蛛:台湾最大的剧毒蜘蛛 被上户蜘蛛咬了会死吗?
上户蜘蛛:台湾最大的剧毒蜘蛛 被上户蜘蛛咬了会死吗?
 灰鲭鲨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鲨鱼 世界最大灰鲭鲨被捕获
灰鲭鲨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鲨鱼 世界最大灰鲭鲨被捕获
 髭蟾:长有"胡子"的两栖动物 髭蟾蝌蚪能长到10厘米
髭蟾:长有"胡子"的两栖动物 髭蟾蝌蚪能长到1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