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住。虽然女生独自居住在安全上有些顾虑,但也不觉得害怕,我总能找到方法替自己排解无聊。由于念书开始就离家居住,所以出了社会之后,在找房子上相当有经验,若是房子有问题或有异状,通常在看房子的当下都能判别一二,也都能避得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出社会的第四年,当时任职的公司给我了一个升迁的机会,唯一的条件是要外派一年,我这个一辈子在台北生活长大的女生从没跨过浊水溪,忽然要下这个决定着实让我考虑了好一阵子,然而机会稍纵即逝。
跟家人讨论过后决定接下这个工作,调整心情就往驻派地开始找房子。找房子不难,难的是怎么找到一个没凶案没闹鬼没恶邻没变态的地点。台台还真是累人。
我的工作地方是当地的热闹地段(嗯,工作跟百货业有关),若是想要在热闹的市中心找到各方面理想的房子得要做足功课,公司不提供宿舍,只给津贴,而“想要“跟“只能要“之间距离很大,我想要的房子地点远,交通不算方便,再加上百货业下班时间通常都是晚上十一点过了,在安全跟便利的双重考量下,我找到了一间离公司步行只要约十分钟路程的房子。
第一次踏进这间房间的感觉就是闷,那种闷并不是天气或水气造成的,而是一种时间凝结于此的窒息感,我本身体质并非敏感类型,从小到大也没遇过什么怪力乱神的事,唸书时期跟同学朋友夜唱夜冲夜游无一不齐,不要说鬼附身,连鬼压床都没有过,总归而言就是大家口中的麻瓜。
所以当时就算感觉很窒闷,我也只是当成空气不流通而已,更何况这房间的前任房客就是带我看房的前辈,她要调回台北,而我正好能接手。我并没有把当时的感觉说出来,前辈似乎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怪异的地方,若真要说的话,就是签约那一刻,她那微微松口气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那股怪异的感觉就让我这样矇混过去了。搬进去住的第一个月平安无事,房间也让我逐步改成舒适的小窝,房间的天花板有一座颇典雅的小吊风扇,有几盏光线柔和的灯光,使整个房间看起来很温馨。
我开始进入工作轨道,也慢慢得心应手,当然随着忙碌工作而来的疲倦也有增无减。就这样周年庆来了。在百货业待过的人都知道周年庆有多重要,这也是我调到这里来的第一个所要面临的挑战,我把我的组员工作调配完毕,开始迎战周年庆人潮。
想当然尔,每天回到家就是呈现死狗一隻的状态,每每卸妆洗澡完毕之后,就死死昏昏去了。在那阵子我却开始睡不安稳,总是睡不沉,彷彿睡着了,但又没有真正睡着,时常做梦,醒来又不知道自己梦见了什么。
某天特别疲累,进了房间之后不知为什么有些出神,就拎着宵夜背着包包站在吊扇底下发楞。头上的风扇一直在转动,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打开它的,同时感觉有股奇妙的触感拂过我左边的脸颊,一下一下地,像是台台羽毛或类似的东西就这样轻轻呼地过去。后来我才注意那规律的触感就跟我头顶上的吊扇一致。于是,我抬起头看向风扇。台台什么都没有。
只有吊扇转动时那微微发出的声响,轻轻地”塔!”、”塔!”当下我忽然清醒过来,为什么我会就这样站在这里?我到底在做什么?看看手上早就冷掉的宵夜,一直理不出头绪。然而,从那天起,每天下班我就会像这样回到家就站在风扇下方发楞,时间则是不一定,
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十分钟,而过程我完全没有自已的意识。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有一个,我左边的脸颊似乎比右边的看起来要黑一点。那并非是晒黑的痕迹,而是整整齐齐从中间为线,明显地黑了两个色阶。
这情况一直到了某天,总公司派员下来查补,刚好是我之前单位的同事L,她事前打电话跟我约时间吃饭,L表示出差不想住饭店,想来跟我挤一晚。我当然表示欢迎,自搬来这里还没有客人踏入,于是当晚我们的工作完成,开心地去买了一堆食物饮料要来好好聚聚。
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任何人,觉得没必要,因为又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所以我像平常一样边找出钥匙把房门打开还一边跟L说笑,打开门的那瞬间,原本还有笑声的L这时在我背后狠狠地倒吸一口气,整个定住不动。
我一如往常走进房里,自然而然地走到风扇底下,接着台台我又出神了。在这中间其实我并没有意识自己做了什么,就只是好像走到吊扇底下发楞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我不知呆了多久,忽然被一股强大的力气拉起手臂,接着用力一扯,整个人被一口气往大门口拉扯出去,这其中发生的时间非常短,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等我记起来要挣扎时,我已经被L拉到大马路上了。
我才要开口抗议,L冷不防地狠狠抽了我一巴掌,左边的脸颊传来了清脆的拍打声,同时爆开剧烈的疼痛,这时我的嘴巴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不要妨碍我!“那个不是我声音的我说。
“你不要附在我同事身上!她又跟你无冤无仇!“
“你不要管!不关你的事!“那个冷漠的声音继续说,此时我有一股很微妙的感觉,像是在隔着很远很远的空间看着我自己在跟别人对话的舞台剧。L一直对着我叫骂,而“我“似乎也不甘示弱回骂,内容我实在记不清,当下的场景若是旁人看起来会以为是正宫跟小三在抢男人。
后来L不耐烦,从她的包包里找出一串佛珠,直接又往我脸上甩过来,说真的L的动作实在又快又俐落,那串佛珠在她手上看起来像是甩鞭的动作,而佛珠打在我脸上的感觉居然不痛?
但“我“的口中却一直发出惨叫,随着她一下又一下地甩,我的惨叫声逐渐变小,直到变回我自己的声音为止。
“怎台怎么回事?“我被打的跌坐在地上,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除了满头雾水还是满头雾水。
L只是苦笑说:“看样子你今天要跟我去睡饭店了。“
到了饭店,L似乎精疲力尽,洗完澡整个人呆坐在床上,她只叫我去泡个澡,而且拿了一包不知是草药还是香料的东西给我,叫我放到热水里一起泡。我只想快点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她却坚持我一定要先泡澡,直到她满意为止,虽然我心中大概有个底,但仍迷惑不已,我根本不觉得我碰上灵异事件了。
等到这些都处理完毕了,我们才开始吃那个冷掉的宵夜跟不凉的啤酒。L一开口没有解释事情经过,反而说:“我家是开宫庙的,就是替人问事的那种。“我眨眨眼,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你一开门,就有一股超难闻的臭味衝出来。“L皱了皱鼻子,好像那股味道还在。
我马上抗议,“我每天都有打扫吔!“
L没有理我,接着又说:“然后我就看见祂了。“
哪个他?我用眼神询问L。
“是个女的,就倒吊在你的风扇叶片,你一进门就什么也不做地站在转动中的风扇底下,那女鬼随着风扇转动,伸出长长的舌头一直不停地舔过你的左脸。“L像是在讲厕所马桶不通所以很臭这种小事般的口气。
我当下的脑袋是一片空白,有个倒吊的女鬼每天舔着我的左脸,当我终于意识那是多么恐怖的画面时,整个人尖叫到差不多有人要去报警的程度。(事实上的确也有房客打电话给柜台)
等我冷静下来后,边抖边问为什么,L表示她也不知道,她只是做了一些紧急处理,但事情还没完全解决,她只是用保身的佛珠暂时赶跑它。L提议说要不要让她家的神明处理看看,此时我已六神无主,虽然什么都没看见,但却又真实发生,我二话不说马上答应,L打电话回家说明此事,表明天亮后就会过去。
L又拿了一张用护贝加护的符纸让我压在枕头底下睡,我原本以为我睡不着,发生这么诡异的事怎么可能睡得着?但我居然睡着了!头才一沾枕,就有一股浓浓的睡意袭来,临睡之前,我还听见L的声音说:“门不知道挡不挡得住。“
这晚我睡的非常安稳,一夜无梦。早上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但L却像打了一晚上的仗一样,看起来非常憔悴。她挥了挥手说:“没事,喝个鸡汤就好,快去请个假,把这事处理掉。“一到L家,她爸爸像是准确知道我们到达的时间,早已气定神閒地背着手等在门口。一下车,我忽然不想靠近了,脚步不自觉地慢下来,L像是发觉了什么似的,抓住我的手臂,说:“不要输给它,走!“
她坚定地抓住,我也只任由她拉着往前走,但心中那股抗拒的感觉愈来愈大,一直走到L的爸爸面前,我根本就想要转身就跑。“都到这里了,还不安份?“说着,L爸爸按住我的肩膀,我居然不由自主地腿软,站都站不住,L适时在我屁股下方摆上椅子,我就这么一咕噜地坐下。
L爸爸面目很祥和,隐隐散发着一股威严,他开始进行一些看不懂的仪式,这边就不提了,因为看不懂就很难叙述。期间我只感觉自己的左脸颊很灼热,而且一直发晕,很努力撑着不要昏过去。折腾了一段时间,脸上的灼热感渐渐褪掉,L爸爸给了我符跟一包草药(跟L给我洗澡的东西一样),交代我回去之后要怎么处理。
后来?后来我回去把L爸爸教的方式淨化房间,接着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前辈,质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接下来的后续发展让我傻眼,前辈调回台北后不久就离职了。据说是因为生了怪病,左脸长了像是疮一样的东西,而且溃烂不止,而我再也没有见到前辈。我一直住在那间房直到外派结束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灵异事件。除了左脸偶尔会发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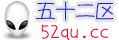
 越南东涛鸡 鸡爪和人手臂一样大
越南东涛鸡 鸡爪和人手臂一样大
 盘点动物界的巨无霸 蓝鲸毫无疑问居榜首
盘点动物界的巨无霸 蓝鲸毫无疑问居榜首
 真正的大长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
真正的大长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
 世界上最大的犀牛 武装部队24小时保护!
世界上最大的犀牛 武装部队24小时保护!
 龙趸是什么鱼?马来西亚发现龙趸王重达400斤
龙趸是什么鱼?马来西亚发现龙趸王重达400斤
 世界上最聪明的猫排行榜 加拿大无毛猫智商爆表了
世界上最聪明的猫排行榜 加拿大无毛猫智商爆表了
 西施狗为什么要叫西施?西施狗多少钱一只?
西施狗为什么要叫西施?西施狗多少钱一只?
 上户蜘蛛:台湾最大的剧毒蜘蛛 被上户蜘蛛咬了会死吗?
上户蜘蛛:台湾最大的剧毒蜘蛛 被上户蜘蛛咬了会死吗?
 灰鲭鲨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鲨鱼 世界最大灰鲭鲨被捕获
灰鲭鲨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鲨鱼 世界最大灰鲭鲨被捕获
 髭蟾:长有"胡子"的两栖动物 髭蟾蝌蚪能长到10厘米
髭蟾:长有"胡子"的两栖动物 髭蟾蝌蚪能长到1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