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年以来,我都在Muskoka(Muskoka 马斯科卡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的一个市)担任一个过夜营队的辅导员。跟我做过的其他工作比起来,我简直是爱死了这份差事。
尽管薪水微薄,有些参加露营的人很烦,必须醒着的时间太长睡眠时间又太短,食物也难吃的要命…但其中一个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说任何只要我挤得出来的恐怖故事。
告诉你们,没有什么比和一群国中小鬼头围在快要熄灭的营火旁讲鬼故事更好玩的了。他们总是喜欢要求听最恐怖,最血腥的那种,所以我就全都说啦,包括保母和恶心的小丑雕像,驾驶和行径诡异的加油站员工,还有小女孩和她那只爱舔人的狗。
我把我最私藏的故事留给在 Algonquin Park(Algonquin Park 阿冈昆公园–安大略省最早设立的省立公园 )过夜时的营队。给非加拿大人的板友,这是一个位于安大略省中部的庞大公园,佔地约八千平方公里。
我们白天在 Pristine lakes(Pristine lakes 阿冈昆公园里的湖泊之一 ,S'mores 用两片苏打饼干夹着棉花糖和巧克力烤的一种甜食,北美的特色美食,跟烤棉花糖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露营伙伴)划独木舟,晚上则围着营火活动,我们一边烤S'mores一边放声高歌,尽管尽情喧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是这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人。
当这些孩子安静下来,我就开始告诉他们在树林里躲藏的跟踪狂的故事,他的面孔是如此骇人以至于受害者们恐惧到无法动弹,或者我会说另一个关于一群露营者决定在夜晚渡过湖面,前往对面一间废弃 (或是没有?)的疯人院探险的故事。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结束了所有故事后,我再次强调这些通通都是真人真事,然后把这些小鬼赶进他们的帐篷。一整天下来大家都精疲力尽,显然的这六个小朋友也没有要熬夜下去的意愿。我的辅导员同事决定回帐篷里休息,留下我独自坐在圆木上,只剩快熄灭的营火陪伴。我深吸了口气,感觉到冰冷的凉意里充满松树的清香,接着我往湖的方向望去。
部分的月亮映照在清澈的湖面上,在湖的尽头,我可以看到高耸的峭壁,向上攀延数百迟。我暗忖着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办法划独木舟过去,爬一点点山路然后从上面的悬崖跳水进湖里。我笑了一下,营队主任铁定会砍了我的头,当然是如果他有发现的话啦。

在最顶端的峭壁上,有些动作攫取了我的视线,我看到一些微弱的光芒延着山稜轻轻摇晃着,一开始我以为是星星,但是它大多了而且闪耀着金色的火光。光点慢慢的来回摆动,呈现一个小拱门的弧度,当我坐挺身仔细瞧时,另一个光点出现了,延着峭壁的顶端微微摆动。然后另一个,再一个,又陆续出现了几个光点。
我的胃感觉像沉到脚底,我抓住我的包,从里面抽出数码相机,对准闪烁着的光球使用放大功能 (zoom function),我数了一次,然后再数了一次。
"喔该死。"我立刻站起来冲向帐篷。
"嘿伙伴们? 快醒来我们得走了。 "
帐篷里有些许的骚动,然后共有七个疑惑的脑袋盯着我瞧。我的辅导员同事的脸上混杂了担心和全然的愤怒。
"我也不想这么做。 "我继续说。
"但远方的云看起来会威胁到我们,有阵豪雨要来了,如果碰上,这个旅程就完蛋了。 "
"你是认真的吗 ?"Laura,我的同事问。
"我们现在在树林里耶,要往哪里走 ?" 我从包里抽出地图和手电筒。
"距离我们南边几公里处有个巡守队的哨站。 " 我的手指追踪着地图上的路线,感谢老天爷。
"我们能够在几小时内抵达。 "小鬼们开始抱怨。
"我们不能等到天亮再走吗 ?"
"不行 !" 我大吼。声音穿越了湖面产生回音。我放低音量。
"走啦,我会在去的路上再说个故事给你们听。"我微微一笑,但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嘴唇在颤抖。
"保证是最棒的故事。 "
这招看起来奏效了,十分钟之内我们打包好所有的营帐,靠着少少的手电筒作向导,开始一段进入树林深处的跋涉。当我确定我们正往平稳的地方前进,我终于允许自己放轻松一点,然后开始讲这个我最喜欢的营火故事。
在欧洲的开拓者进入这个国家的几世纪之前,这里是原住民的栖息地。他们长途跋涉,跟随着大型动物,例如水牛和美洲野牛的迁徒路线,横跨过加拿大西半部。终于,他们抵达了安大略,在某个时间点,这群人决定分道扬镳,分裂成为较小的团体,每个团体都想要找到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传说是这样的,其中一个由二十几名男子,女子和小孩组成的团体,为了找寻心目中的理想家园,探索到我们现在这块气候极端的地区。尽管还没接近十月底,天气逐渐使这段旅程难上加难,当这个团队远征至湖的周边时,一阵猛烈的暴风雪开始重击山区。
不到一个小时,这群人发现巨大的风雪笼罩住整个山头,这几乎使他们眼盲,温度也骤降至零度以下。他们身上的衣服是为了秋天做的,不适合这种气候,当然那时候可没有Canada Goose。(Canada Goose-加拿大极富盛名的羽绒外套品牌,以保暖和高品质闻名,不只加拿大,在美国和欧洲也很常见。)
但这群迁徒者仍继续前行,他们没有其他选择的馀地。当他们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壁时,夜幕降临大地,这个峭壁耸立在冰冷澈骨,波涛汹涌的湖面之上,不翻越过这座断壁就只有死路一条,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加上逐渐增强的暴风雪,视觉能力已经可以说是完全不复存在。
其中一位长者想出一个方法,他用所剩无几的煤油,为每位成员点亮一个灯笼,并要他们拿在面前。这么做不只能看到峭壁,还可以看到自己前面的人,允许他们跟着前一人的脚步穿过狭窄陡峭的山路。
由最强壮的男人领队,他们开始翻越山头。那结冰的湿冷风雪渗进他们的每ㄧ吋肌肤和骨头里面,呼啸的暴风降低他们所有曝露在外的皮肤温度,威胁着要将他们狠狠吹下这块巨岩。能够踩踏的道路不过几迟宽,就算穿着最好的登山靴仍湿滑无比,更不用说手做的莫卡辛鞋了。非常缓慢,小心翼翼的,他们爬上绝壁,祈祷着对面不管是什么都好,只要能让他们作为临时避难所,逃离这场恐怖的暴风雪。
虽然没有人看得到前方,他们还是跋涉了大概一半的路程,爬到离湖面约数百迟的高度,事实上,在这密集的风雪中,他们唯一能够辨识的仅有前方伙伴手上的灯火,像是扮演着灯塔的角色,引领他们的脚步。当光点朝上移动,后方跟着朝上,当光点往下,后面跟着往下。
所有的人彷彿都被催眠一般,什么都不重要,只在乎离自己几迟远外的闪烁球体。但带头的领队可就没这么奢侈的待遇,他以几乎全盲的视线蹒跚前行,尽管肌肤已麻痺到几近无知觉,仍尝试用所有的感知判断崖线的走向。
山路蜿蜒,突然,他不小心踏错脚步,整个人失去重心,受诅咒般的,一阵巨风忽然用力刮起,猛烈推向他的背,他急切的想要抓住什么来撑住自己的身躯,但冻僵的手指却只抓到一场空。伴随着妻惨的尖叫声,他从峭壁上失足并掉落进漆黑的冰湖里。
其余的人当然没看到他摔落山崖,他们只看到亮着的光点从崖壁上掉落,接着消失在黑暗之中。没有哀悼的时间,他们继续前行,气候却是更加恶化。
不久之后,一个小孩,他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寒冷,他从队伍中滑落,手上的灯笼持续燃烧着直到翻涌的湖水将之扑灭。另一个成员,目睹了这个孩子的死亡,自己也突然失去平衡而摔落。这个形式不断的重複,直到只剩下五个人存活,他们笨拙的在无边黑暗中摸索,紧紧跟随着前方的光。
尽管奋力的尝试,这座断崖仍然不肯饶恕他们。幸存者掉落至四个,接着三个,然后两个,最终,只剩下那孤独的一个人,传说当这一个人的脚因没站稳而摔落时,他大声的咒骂这个世界直至无底深渊,他的灯笼是最后一个被熄灭的。
"这二十个人极力的想要克服这些峭壁。 "我结尾道。
"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存活下来。"
"直到现在,听说只要情况对,你仍可以看到那些在峭壁上闪耀的光点,象征着这群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梦想家园,永远迷途的迁徒者。 "
结束这个故事后,所有的孩子都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当我看到前方有光,安心感瞬间排山倒海而来,我们加快脚步找到巡守员的哨站,发现他们正飞快的动员脚步,约有六个人跑进跑出,边将卡车装满边对着广播吼叫,我感觉到风开始颳起,也听见了远方轰隆隆的雷鸣。
“喂,小鬼们! ”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朝我们跑来。
“快上车,我们时间不多了。 ”Laura和我引导着孩子们上卡车。
“发生什么事 ?”我问这个大叔。
“你们没听到吗 ?”另一个粗犷的声音回答。
“一个巨大的暴风正朝我们的方向扑来,龙卷风已经着陆了,我们要把所有人都撤离这里,快走吧 !”
我们全都爬进卡车,我整个身子摊软在座椅上,感觉像是有人狠狠朝我的内脏揍一拳。巡守员也爬上前座,当我们驶进一条捷径,我开始感到头晕,这不可能 …
“你怎么会 …”Laura滑到我旁边,用着很小的声量开口。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必须离开那里 …?”我看着她,知道我的脸上肯定毫无血色。
“我看到那些光了。 ”
“什么 ? 不,不会吧 ?”她惊喘,然后镇定下来。
“多少个 ?”我深吸一口气。
“八个。 ”
她转头看了下所有的孩子,他们现在正互相倚靠着,虽然山路颠簸仍沉沉陷入梦乡。
“那就是我们全部 …我的天啊 …”
我点点头,和她相依着沉默不语。Laura之前听过这个迁徒者的故事,也知道我只陈述了部分的事实。没错,灯火的故事是真的,但他们绝对不是偶然出现的。如果你看到火光闪烁,轻微的前后摇晃,并摆动成一个小小的拱形,那代表着一个信息,一个警示。一个燃烧的灯火,代表着一个即将熄灭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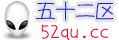
 越南东涛鸡 鸡爪和人手臂一样大
越南东涛鸡 鸡爪和人手臂一样大
 盘点动物界的巨无霸 蓝鲸毫无疑问居榜首
盘点动物界的巨无霸 蓝鲸毫无疑问居榜首
 真正的大长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
真正的大长腿!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
 世界上最大的犀牛 武装部队24小时保护!
世界上最大的犀牛 武装部队24小时保护!
 龙趸是什么鱼?马来西亚发现龙趸王重达400斤
龙趸是什么鱼?马来西亚发现龙趸王重达400斤
 世界上最聪明的猫排行榜 加拿大无毛猫智商爆表了
世界上最聪明的猫排行榜 加拿大无毛猫智商爆表了
 西施狗为什么要叫西施?西施狗多少钱一只?
西施狗为什么要叫西施?西施狗多少钱一只?
 上户蜘蛛:台湾最大的剧毒蜘蛛 被上户蜘蛛咬了会死吗?
上户蜘蛛:台湾最大的剧毒蜘蛛 被上户蜘蛛咬了会死吗?
 灰鲭鲨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鲨鱼 世界最大灰鲭鲨被捕获
灰鲭鲨是世界上游速最快的鲨鱼 世界最大灰鲭鲨被捕获
 髭蟾:长有"胡子"的两栖动物 髭蟾蝌蚪能长到10厘米
髭蟾:长有"胡子"的两栖动物 髭蟾蝌蚪能长到1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