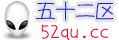这是在我小学六年级发生的事,四月中旬的某天放学时,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教室清扫,因为我不小心打破花瓶。
班导帮我处理玻璃后,叫我把溼答答的地板清干净。因此当我走出校门时,已经晚了其他‘直接回家小队’的人几十分钟。
昨晚下过很大的雨。种植在校园里的樱花几乎都被打落,路上花瓣四散,脚边的水洼变成了粉红色。
平时我总是完全不在意水坑直接踩过去,那天却小心翼翼的闪避著通过。
回家路上,我如往常般经过幼儿园的时候,路边有个人抬头往上看着生长在园内的大杉树。
是跟我同校的学生吧,背着黑色书包。
我记得这张侧脸,他是开学典礼那天转来我们班的学生。
是个特立独行的转学生。
转学第一天的下课时间,他都没有待在教室。
一下课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出教室,不知何时人就不见了。隔天也是如此。
对转学生而言,转学第一天是结交朋友最关键的日子吧。
重要的下课时间却自己离开教室,于是其他人就认为他是个讨厌人群的怪咖。
这个转学生就在我面前,往上盯着杉树。
在园内有玩着小型游乐器材的孩子们与看着他们的保育员老师。
我以前也像这样在这里玩耍。
我是个非常喜欢幼儿园的小孩,即使是假日我还是会哭闹著说“不要─我要去幼儿园!”,让爸妈觉得困扰。
杉树长在园内角落,一定是在这座城镇形成前就在了吧。树干很粗,高度是附近民宅的三倍高。
它不像建材用的杉树那么笔直,外观看起来有如抱着身体的人;树下挂著一张写着‘守护杉’的名牌。
我还是幼儿园学生的时候,那棵树就已经被叫做‘守护杉’了。
从转学生旁边走过,我也往上瞄了一眼杉树。
他到底在看什么呢?默默猜想应该是在看停在树枝上的鸟吧,结果不是。
一双白色鞋子,浮在空中。
不可思议的景像。
我继续前进,脖子一直跟着那双鞋转动,到了脖子转动的极限后我停下脚步。
把身体转向杉树,再看一次。
一双白色运动鞋,脚尖往下,浮在比我头还要高的地方。
再往上一、二公尺有很粗的树枝横向长著,应该是从那里用细绳吊著吧。
可是,为什么呢?
等我注意到时,刚刚还在抬头看杉树的他不知何时迈开脚步。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般,淡然地从我旁边走过。
我转过身,想开口叫住他。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我犹豫不决之间,他已经弯过转角,失去踪影。
被独自留下的我,再度抬头看向杉树。
什么也没有。白色鞋子消失了。
我呆立在原地,茫然看着杉树。
幻觉、错觉、看错了。但如果是我看错了,那他到底在看什么呢?
那天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了今天的事。
一双白色鞋子,浮在幼儿园的大杉树下。
准备要去买晚餐材料的老妈,走向玄关时拨乱我头发,说了句:“别说傻话了”
到了隔天,我在上学途中经过幼儿园时,抬头看那棵杉树。
不见白色鞋子的踪影,我更换角度、瞇着眼仔细看,还是什么都没有。
回过神,栏杆的另一边有个红著脸颊的小男孩觉得奇妙似的看着我,我假笑了一下,迅速离开。
果然是看错了。
像老妈说的,是我耍笨。
感到有些放心的我,接下来的日子都没有再想起白色鞋子的事。
之后又过了段时日,四月结束,时间来到五月,很快就是端午节。
那天的前一天也下过雨。
放学后我独自回家,路上有许多因大雨遗留下的水洼。
我边走边故意去踩,水花四溅,连袜子都湿掉。随脚步响起的啪搭啪搭声让我玩得很开心。
我打算跟老妈说是我不小心掉进水沟。
就这样,我来到幼儿园前的道路。
我停下动作站着。是因为我听到什么了吗?还是第六感?理由我已经忘了。
总之我停下了脚步。
往园内看,正好就是那棵杉树,好像要挡住我视线一般。
突然想起白鞋的事,我的视线不知不觉沿着树干,往上方移动。
白色鞋子就浮在我头上。
我看着那个,连眨眼都忘了。
有人穿着那双白鞋。
看到的不只是鞋子,之前没看到的人的脚踝,是人类的脚穿着鞋。
断在小腿的部分,再往上就看不见。
颜色和轮廓雾濛濛的,可是那二只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的确浮在空中。
有人从我背后走过。
我猛然往旁边看,黑色书包正要弯过对面转角,是我见过的那个背影。
“等一下!”
我立刻叫住他,他停下来,慢慢转向我这里。
那张脸面无表情,如往常一样看不出来在想什么。
转学到这里以来的一个月,他被大家当做是教室里的摆饰一样。而他在下课时间也同样不会待在教室。一开始还有人觉得这沉默寡言的转学生很有趣,习惯后就没人想找他了。
他安静的看着我。
没办法用言语表达,我无言的往浮在杉树下那双不知道是谁的白色鞋子一指。
他朝我指的方向看去,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看得到?”
他抬头望着杉树开口。
虽说不太可能,但我发现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白色鞋子、还有脚踝”
我照我看到的来回答。
看来他也看得到一样的东西,应该不是在假装。
“是吗。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再看了”
接着他慢慢看向我。
“那个人、在看你”
说完这句话,他转身离去。
我没有再出声叫他,看着他走掉。
等他的身影消失于转角,我往上看着杉树。
白鞋和人的脚踝,突然不见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回家我也向爸妈报告这件事,果然他们二人都没有认真理会我。
不是我看错,我很想知道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我几近确定的认为他一定知道些什么。我看到二次白色鞋子,第一次跟第二次他都在我旁边。
而且,最一开始是他先往上看着杉树的,不可能跟他没有关系。
隔天学校午餐时间结束、午休时间开始时,我比其他人更快跑出教室,在走廊等著。
他像平常那样走出教室,我抓住他的肩膀。
“可以跟你说一下话吗?”
他默默看着我。一样保持面瘫,是觉得麻烦吗?
不管他到底在想什么,我对着一言不发的他展现出我自己觉得最和善的笑脸:
“在你说好以前我都会一直缠着你”
他垂下头,轻轻吐了口气。
“……好”
我们来到没什么人的中庭。走下台阶,将室内鞋换成外出鞋后,走到外面。
坐在浮着睡莲叶的圆形水池外缘,我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地问他:
“那双白鞋子和脚踝,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很简洁。
然后,他接着说:“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
‘那个人’,之前他也这么说。还叫我‘最好不要再看了’
不只有脚,一定还有上面的部分。而且他也看得见。
“那个人……。人会在那种地方做什么啊?”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看着水池中心喷水的地方。
“不要再接近我比较好。尤其是你”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想开口时,他抢先一步说:
“因为我有病”
就像在读稿的新闻播报员一样,他的语气一贯平淡。
“……有病?”
“你有在自己家浴室看过水母漂浮着的景像吗?”
那一瞬间,我听不懂他在问什么。认真思考后,我沉默的摇摇头。
泡在浴室里的水母。我怎么可能会看过。
“我得的就是看得见那种东西的病。你看到的白鞋还有脚也是”
所以他是‘自称看得见的人’,而他自己也说出了原因。
生病。这虽然无法全盘解释我遇到的事情,却有某种说服力。
至少比起那些总是在电视上说自己看得到幽灵还是鬼怪却不解释原因的什么灵能力者,他的说法更能说服我。
“你被我的病传染了。之前偶尔会出现这样的人。……你并不是从以前就看得见的吧?”
传染病。他说我会看到那双白色鞋子,是因为我被他的病给传染。
我们得了同一种病。
或许是因为我的样子看起来惊慌失措,他像是要让我安心一样,很勉强似的露出一个还算能辨别的微笑。
“没问题的,只要不接近我,这个病自然就会治好”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他离开中庭,我都还坐在喷水池旁边。
下午的课我也心不在焉,没听老师在讲什么,也没看黑板。
我当时大概是在思考什么吧,可我不记得内容了。
那一天的课只有五小时,学校比较早放学。
放学时我婉拒了跟朋友一起回去的邀约,比其他人稍迟一些踏上归路。
漫步走着,我来到那棵杉树所在的幼儿园前。没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应该正值午休时间吧。
这棵树的树龄几年呢?我站着,头朝上往杉树看去。
此时此刻我没看见任何常理无法解释的东西,映在我眼中的只有往空中生长的杉树以及更上面的蓝天而已。
就这样回家的话,还能如往常一般平稳的过日子吧。
我很清楚这件事,但我没有离开,不,应该说我走不了。
背着黑色书包的他走向这里,看到我,啪搭一声停住。
一样面无表情让人看不出想法。不过他会停下来,是对于我居然出现在这里而感到意外吧。
“欸,来这里一下”
我举起手说著。花了一些时间,他来到我旁边。
“……怎么了?”
我不理会他的问句,往上看着杉树。
我刚才绝对没看到的白色运动鞋、脚踝,上面出现了膝盖跟短裤下摆。
果然没错,因为他在旁边我才看得见。而且看到的范围比昨天更广。
“要怎么做才能更清楚的看见?”
我盯着上方看,问他。
“……不要看比较好”
他重复著昨天说过的内容,我没有接话。
我们维持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终于放弃似的轻呼出一声叹息,和我一样抬头看着杉树。
“昨天是只有鞋子和脚踝对吧。现在呢?”
“现在到膝盖附近”
“短裤呢?”
“稍微、看得到”
“这样啊……”
下一瞬间,他的右手握住我的左手手腕,让人毫无心理准备、唐突的举动。
我惊讶的看着他,他的表情不变、视线固定在杉树上,接着他用空出来的手往上一指:
“你看得到那个人的手吗?在裤子腰身那边、摇晃着的白色的手”
尽管觉得困惑,我还是朝上看去。
看到手了。
只有手腕到指尖的部份,却很清楚。像他说的一样是白色的手。
因为他握着我的手,现在我不只看得到短裤下摆,腰部附近也能看得见。
“穿着很像斑马条纹的长袖上衣对吧”
他在我旁边说完这句,我的眼睛马上看见模糊的黑白条纹上衣。
逐渐变得鲜明,连衣服皱褶都一清二楚。
随着他一句句详细说明,我能看见的‘她’的部份越来越多。
“脖子,被绳子勒住”
我看到绳子了。在伸出的树枝上有条绳子垂吊著,绕在白色脖子上。
“是个女人,短发、稍微吐出舌头,眼睛……在看着你”
说完最后一句,他放开握住我的手。
看到脸了。
我全部都看到了。
那双脚、手、身体、脸、口中微微吐出的舌头、
还有那眨也不眨看着我,空虚的眼神。
“……啊”
我不禁叫出声音。
为什么我现在才发现呢,我认识这个人。
她是我就读这所幼儿园中班、大班时,照顾我的老师。
我小时候,妈妈不断进出医院,年幼的我总是很寂寞。我应该是想从老师身上寻求妈妈没办法疼爱我的情感吧。
我当时很习惯巴着她的腿不放,像猴子还是无尾熊的婴儿那样。她也让我抓住她的脚,就这样“嘿咻嘿咻”的走着,去忙别的事情。
是个很温柔的人。
而这位老师上吊死了。
我抬起手,碰触白色运动鞋,指尖摸到了却没有感觉,我的手指在空气中抠著。
我碰不到。
“没事吧?”
他是在担心我吗?
“……是我认识的老师”
我用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的冷静声调回答。
真奇怪,就算老师的尸体在我眼前,我还是没有什么实感。
就像看到电视里的名人在举行丧礼那样。
被绳子吊在树下的她,一直看着我。
我和老师认识的事情,说不定他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叫做‘守护杉’对吧、……这棵树”
他在我旁边小声的说。
后来,我在哪里跟他道别、又是怎么回到家的,我都没有印象。
我回家问了妈妈这件事。
说出老师的名字后,妈妈总算坦白。之前不说是觉得我就这么忘了会比较好吧。
老师是自己走上绝路的。
因为失恋而自杀,时间是在我从幼儿园毕业没多久后。
她的恋人是当时在同一所幼儿园工作的同事,我也记得那个人。
分手的理由不是吵架也不是劈腿,原因是出在老师所出生、成长的故乡。
被人们厌恶、避之唯恐不及的土地。
我知道这说法,但那根本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深切的认为这么做毫无道理。
妈妈说:“那时你有一阵子、都会叫那位老师‘妈妈’呢”,很怀念似的笑了。
我回忆中老师的样子慢慢和眼前的妈妈重叠。
泪水擅自从我的眼眶一滴滴滑落,老师已经死去的实感终于出现。
我像小孩一样的哭了。对这样子的我,妈妈摸着我的头。
到了隔天,我在上学途中绕去幼儿园。
门旁站着一位保育员,我把前一天妈妈帮我准备好的一小束花拿给那个人。
在我拜托保育员将花束供奉在杉树下后,这位有点年纪的保育员便了然于心,一瞬间浮现高兴却又寂寞般的表情。
“谢谢你”
她对着我说。
我看了杉树一眼,没有见到老师的身影。
背对幼儿园,踏出脚步。我没有流泪,为老师流的泪似乎昨天就已经全部流光了。
在通往学校的道路、小学校门口前,我看见眼熟的黑书包。
是他。
我张嘴想叫住那个背影,却说不出话。
停下脚步,我直直站在原地。
他生的病。
‘不要靠近我比较好’他说的话。
从上方俯视着我的老师的眼神。
看得见那种东西。
一堆话语和事情在我脑中打转,我犹豫着该不该追上那个背影。
觉悟,应该可以这么说。不过当时的我还没抱着那种想法。
因此,我开始叫他‘水母’,是在不久之后的事。
有人从后方拍了下我的肩。
“呐、为什么站着发呆?”
转过身,同班的女孩子头上冒着问号看我。
我有点慌张的回答:“什么事都没有”;她更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说:
“你是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吗─?”
说完便天真的笑了。